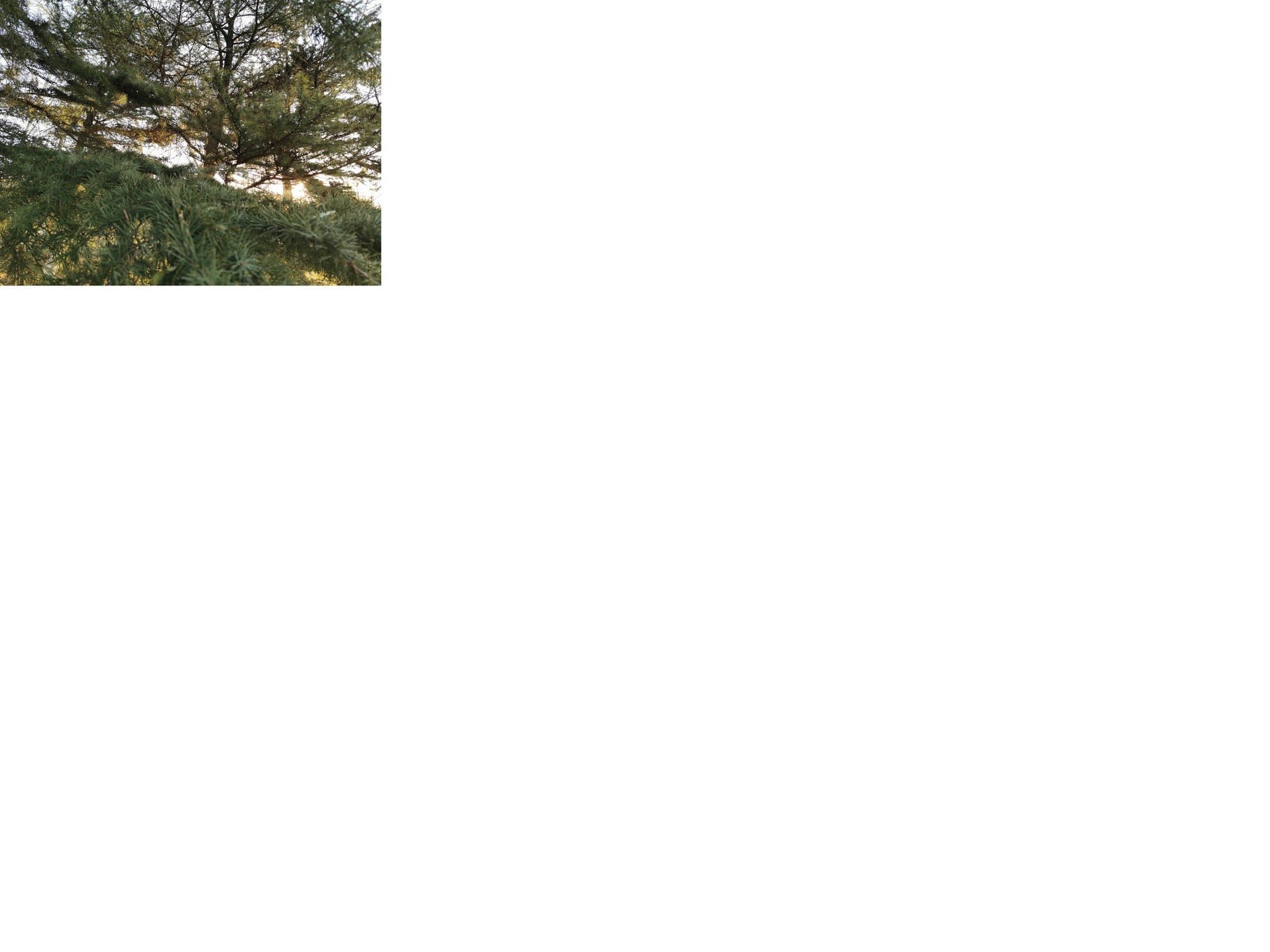就 义
作者:一抹红霞
一九三五年秋,清乡队的后院的磨坊里,关押着被捕十多天的我已是遍体鳞伤,衣衫褴褛。
一清早,我开始收拾自己,梳理蓬乱的头发,整理破烂的衣裙,做临刑前的准备。
国民党鄂西北剿匪总指挥部昨天就已经给清乡队下达命令,要在今天上午午时之前将我绑赴北门外刑场执行死刑。
窗外已是黎明时分,远处的鸡叫此起彼伏,这是我最后一天听到鸡叫,明天这个时候,我已经告别人世了。
我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墙角,用瓦盆里的水洗了洗脸颊。
这时,听到院子里有走动的脚步声和低声说话的人声,我知道,敌人来押解我了。
不一会儿,牢房的门开了,一个穿着黑布衫的彪形大汉带着两个喽啰走了进来。
黑布衫的彪形大汉一进门就冲我喊道:“刘燕春,今天是你的死期,你要老老实实配合,不然,要你死的很难看。”
我一抖手中的镣铐,厉声说道:“共产党员视死如归,要杀就杀,动手吧。” 说着,我伸开手臂,等待他们捆绑。
我被特务连推带搡的拉到院子里。
我看到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便衣和几个县党部的制服人员站在院子中间。一个便衣手里拿着一把麻绳,另一个便衣拿着亡命牌向我走了过来。
黑布衫的彪形大汉从上衣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我手腕上的铐子。
清晨的风有些凉,我只穿了件单薄的丝绸夏装旗袍,没有袖子,下摆在膝部,而且由于在刑讯中打手的肆意折磨,我的旗袍已是血迹斑驳破烂不堪,勉强遮体。凉风一吹,我的胳膊立即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是,为了不在敌人面前低头,我依然挺着胸,昂着头,遥望了泛出蔚蓝色晨曦的天际。
黑布衫的彪形大汉驾着我的膀子,拿绳索的便衣开始将麻绳搭在我的肩头,然后扯过一只胳膊开始缠绕,缠绕到手腕后,将我的手腕交给那个拿亡命牌的匪徒捏着,他又开始缠绕我另一支臂膀。而后使劲将我手臂狞到背后,用麻绳扎紧手腕,在那大汉的帮助下,将剩下的绳索从我脖颈绕过来,再在手腕交汇缠绕后便使劲向上提我的手腕,一直到极限。这才将绳索在我后背中间扎死,打了个死结。
当他们捆绑完毕,我已经感到手腕以下到手指开始发麻。
我抬起头对捆绑我的匪徒说道:“杀一个孱弱的女子,你们用得着捆绑这么紧吗,我不会跑的,能不能给我松一些。”
这个匪徒没说什么,看了看那个大汉。那大汉也不言语,抬起脚猛的踹了我的腿部一下,我一个趔趄,差点倒地。他骂道:“挨千刀的共党婆,还想舒服吗,早干嘛了,闹革命,今天就先他妈的革了你的命,忍着吧,不要一个时辰,你就想胳膊麻也不可能了。”
看到匪徒这么残忍,我知道没必要跟他们说什么,忍着吧,他说的对,等会儿枪一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亡命牌上,我的名字上已经打了红叉,这叫勾红,就是立即处决。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热血直涌,一种为了劳苦大众献身的激情在我胸中汹涌澎拜。
那大汉一招手,拿亡命牌的匪徒走了过来,抬手往我脖颈后面插亡命牌,在他举起亡命牌的时候,我看到牌子上写着:处决,这二字被打红圈圈着,然后是 女共党刘燕春一名。
他们插亡命牌的动作很粗鲁,粗糙的木板把我后背戳破了好几处,最后在我手腕的绳扣处扎紧了。
亡命牌做的很长,插在我后背的有一米左右,从我头部往上露出的亡命牌还有约一米长。
就这样,清乡队长吹响了哨子,匪徒们列队,为首的一个匪徒手里拿着铜锣,两个捆绑我的匪徒架着我的膀子,行刑的队伍出发了。
这时候,天已大亮。
清乡队驻地是过去一家姓杨的大土豪的宅子。这个宅子三进院落,每个院落都是一处四合院,最后一个院落是杂物间和仓库及磨坊和打工人住的地方。后来我组织民众闹革命,把这家的土豪镇压了,房子分给了附近的穷人。后来革命失败,反动派回到县城,将这里的穷人赶了出去,杨家的人都跑到外地去了,这里就成了清乡队的驻地。
我是在革命失败撤退的时候被被捕的。
我被架着,裹挟在行刑队伍里,跌跌撞撞的穿过几进走廊,走出杨家宅子的大门,被从大门口的台阶上推搡着走到街头。
这时候,那个大汉从大门口的墙边提起一个带栅栏的一尺大小的方匣子,走到我面前。大汉晃了晃手中的方匣子对我说:“刘燕春,让你认识我,我就是这宅子的主人杨进财,你杀了我爹,今天我要亲手杀了你,给我爹报仇,看看这个,我要割下你的头到我爹坟上祭奠他老人家,还要挖了你的心供在我爹娘的灵牌前。”
我哼了一声:“这是你们反动派的反攻倒算,你们等着,最后胜利一定会是人民的,你们最终会受到劳苦大众的清算的。”
说完,我奋力甩开架着我的匪徒,挺起胸,昂着头,赤着脚,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迈出了坚毅的步履走向前。
前面的锣声响了,就听那匪徒高声吆喝道:“各位乡党,今日处决女共党刘燕春,大家快去看杀女共党哦。”
开始街边的人还是很稀少的,毕竟是一清早,但是随着锣声和匪徒的吆喝,人们纷纷从四处涌出来,或站在街边店铺台阶上,或立在路沿石上翘首张望着。
当我被押解着走了一段路,拐上大街时,这里已经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声吵杂的情景。
清乡队的人用枪托驱干着拥挤的人群,留出一条通道供行刑队穿过。
看到这一切,我认为是我临死前宣传革命的好机会,我要做最后的一次斗争。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乡亲们,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我就是南坪县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刘燕春。由于反动派的猖狂,我们的工农革命暂时失败了,我们无数个工农大众的先进分子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革命的火种还在,工农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一天一定会到来的。乡亲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我们为了劳苦大众可以奉献自己的一切,我自被捕以来,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折磨我,凌辱我,我都没有屈服,我没有给党给劳苦大众抹黑。”
这时候,我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自己姐姐搀扶着母亲挤在人群里,远处,我的父亲,哥哥也站在一家店铺的台阶上张望着,我看到他们泪眼朦胧,我的心啊:
在这就要离开人间的最后的时刻能够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骨肉亲人,我感到欣慰,同时,又为让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骨肉被折磨的不成人形而且要被拉去杀害,而感到难过。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望着凝望我的母亲说道:“亲爱的亲人啊,永别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女儿好妹妹而骄傲啊。”
我看到妈妈和远处的父亲在擦拭眼泪,我的眼泪也要夺框而出,但是我不能流泪,不能让敌人看到我的柔弱。我大声的说:“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女儿不能在你们膝前行孝了,让姐姐和哥哥替我孝敬你们二老吧。”
这时候,后面的匪徒开始用枪托捶打我后背:“住嘴,不要胡言乱语,疯婆子,死到临头还宣传赤色革命。”
我跌跌撞撞的走了几步,依然昂起头,这时候拥挤的人群里已看不到我的亲人。
我头一扬,高声的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敌人不许唱,不断地用枪托击打我的脊背,我一次次倒下、拉起,我昂起头,继续唱。
县城不大,这样走了一会儿,便来到城门口,这一段路全部是青石条,我的脚镣在青石板上拖的哗哗作响。
走过城门,我被带到城墙下的一片草地上,在距离城墙两米左右的草滩处停下了。
两个匪徒上来摁着我的肩要我面对城墙跪下。
我跪到草地上,等匪徒走开后,我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转过身面对围观的人群喊道:“乡亲们,永别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杨进财手持步枪跑过来,嘴里不知道咧咧说着什么。
我挺起胸,看着他拉动枪栓,知道行刑就要开始了,我奋力高声喊道:“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
杨进财抵近我两三步距离,举枪对准我胸部扣动了扳机。
就听叭的一声枪响,我感到胸口给猛地一击,身子向后一个趔趄,开始天旋地转,我硬挺着想站稳,就在这时杨又开了一枪,我眼睛一黑,噗通一声栽倒在刑场上的草滩里。
我没死,飘起来了;我在空中回眸,看见躺在地上的我,和被鲜血染红的葡匐的野草。